一個語文老師眼里的孩子:從沉默到開口,從慌亂到自信
【來源:易教網 更新時間:2025-10-03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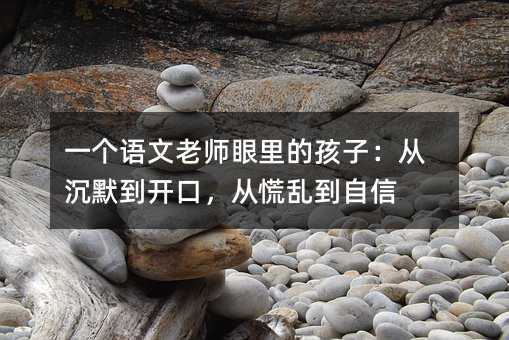
暑假結束前的最后一天,楊邦軍主動舉手,在全班朗讀了一整段課文。聲音不大,但字字清晰。讀完,他沒笑,也沒看我,只是輕輕坐下了。可我知道,這一步,他走了整整六周。
他剛來的時候,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全。拼音混淆,偏旁錯位,作業本上涂改的痕跡比字還多。更讓人擔心的是他從不開口。上課提問,他低頭;小組討論,他縮在角落;下課鈴響,別人跑出教室,他還在座位上慢慢收鉛筆。
我沒有急著糾正他的錯字。我先坐到他旁邊,問他:“你最喜歡哪本書?”他搖頭。我又問:“有沒有哪句話,你一聽就記得住?”他想了想,說:“《小王子》里說,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。”
我沒料到他會說出這句話。后來才知道,他媽媽每天睡前都會念一小段給他聽,哪怕他聽不懂,也堅持念。
從那天起,我不再只盯著他的錯題本。我讓他當“小朗讀者”,每天課前讀一句課文,不計對錯,只計勇氣。讀錯了,我說:“這句話你讀得比昨天穩。”讀對了,我說:“你剛才那句,像春天的風。”他慢慢開始抬頭看人,開始在作業本角落畫小星星,開始在課間主動借橡皮給同桌。
吳思凱的情況不一樣。他聰明,反應快,作業總是第一個交,字跡工整得像印刷體。可他媽媽第一次來接孩子時,眼淚沒停過:“他出生時被羊水嗆過,醫生說可能影響腦發育。我怕他跟不上,怕他以后被人笑話。”
我看了他的試卷,閱讀理解全對,作文結構完整,甚至用了“仿佛”“悄然”這樣的詞。我問:“你平時喜歡看什么書?”他說:“《昆蟲記》和《窗邊的小豆豆》。”我點頭:“那你比很多五年級的孩子都讀得深。”
我跟家長說:“孩子不是有缺陷,他是早熟。他不是慢,他是想得太多。”后來,他媽媽不再問“他會不會落后”,而是問:“他今天開心嗎?”
二年級的孩子,字要一個一個教。六年級的孩子,思想要一點一點引。中間的三、四、五年級,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期。
三年級的孩子,看圖寫話總寫成“今天天氣很好,我看到了一只狗”。我讓他們閉上眼睛,想象那條狗的毛是濕的還是干的?它尾巴是翹著還是耷拉著?它聞到了什么味道?有人寫:“狗的耳朵像兩片被雨打濕的樹葉,一抖一抖地,好像在聽云說話。”我把它抄在黑板上,全班鼓掌。
四年級是作文的分水嶺。很多人會寫“我幫媽媽掃地”,但不會寫“掃帚劃過地面的聲音像老奶奶哼的歌,灰塵在光里跳舞”。我讓他們每天寫五十字的“瞬間觀察”:窗臺上的螞蟻怎么搬餅干屑,放學路上賣糖葫蘆的老人怎么數錢,同桌的鉛筆盒為什么總開著。不求完整,只求真實。
期末,有學生寫了:“媽媽的白發,是夜里偷偷長出來的,我一碰,就疼。”
五年級和六年級,不再教“怎么寫”,而是教“為什么寫”。我們讀《城南舊事》,討論英子為什么舍不得送走蘭姨娘;讀《草房子》,聊桑桑為什么把鴿子籠改成鴿子的家。他們開始問:“老師,人為什么要難過?”“為什么有些事,不說出來更好?”
我沒有用過任何所謂的“高效記憶法”“速成作文模板”。我只做了一件事:讓每個孩子,都有機會被聽見。
有的孩子,需要的是耐心等他開口;有的孩子,需要的是有人告訴他:“你不是不夠好,你只是太認真。”有的孩子,不需要補習班,只需要一個愿意蹲下來聽他說話的老師。
教育不是把空白的容器填滿,而是點燃一盞燈,讓它自己發光。
我見過太多家長焦慮:孩子拼音總錯怎么辦?作文沒結構怎么辦?閱讀理解總丟分?可真正決定孩子未來走得遠不遠的,不是他今天背了多少詞,而是他敢不敢在課堂上說一句“我不懂”,敢不敢在日記本里寫“我今天很難過”,敢不敢在多年后,還記得某個老師曾認真聽過他講的一個夢。
楊邦軍現在會主動問我:“老師,明天還能讀課文嗎?”吳思凱的媽媽發來消息:“他昨天自己讀完了《小王子》,說想寫一封信給狐貍。”
我沒有獎勵他們貼紙,也沒有發獎狀。我只是在他們讀完、寫完、說完之后,輕輕說了一句:“謝謝你告訴我這些。”
這句簡單的話,比任何輔導書都管用。
教育最深的痕跡,不在分數上,而在孩子眼神的變化里——從躲閃到直視,從沉默到表達,從害怕犯錯到愿意嘗試。
這期培訓結束了。我帶的五個年級,六十七個孩子,沒有一個因為“基礎差”被放棄,也沒有一個因為“聰明”被拔高。他們只是,被看見了。
下一期,我還會在這里。等下一個沉默的孩子,開口說話。
等下一個被誤解的孩子,被理解。
等下一個以為自己不夠好的孩子,發現:原來,他早就站在光里。
 搜索教員
搜索教員

最新文章

熱門文章
- 殷教員 中國政法大學 英語
- 嚴教員 清華大學 數學
- 辛教員 新疆大學 師范類物理學
- 王教員 北京語言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
- 張教員 北方工業大學 微電子科學與工程(集成電路的設計與測試))
- 徐教員 香港的大學 經濟學
- 周教員 北京語言大學 英語和高級翻譯
- 陳教員 貴陽學院 漢語言文學
- 吳教員 北京大學 藥物制劑
- 王教員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保險精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