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小學語文教師的自我覺醒:在平凡中追尋教育的溫度與深度
【來源:易教網 更新時間:2025-09-23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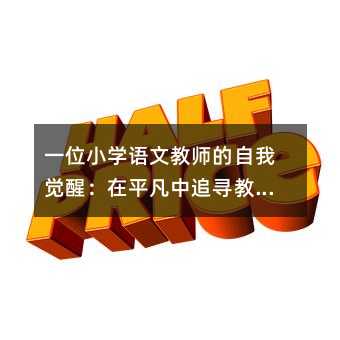
清晨六點,城市還未完全蘇醒,我坐在書桌前翻開一本泛黃的《給教師的建議》,窗外微光初現。這樣的時刻已經持續了整整三個月。作為一名執教十余年的小學語文教師,我曾以為自己早已熟悉講臺的節奏、教案的結構、考試的重點。
但就在某個批改作文的深夜,當我看到一個孩子寫道:“老師,我覺得你上課像在念說明書”,我的心猛地一沉。
那一刻,我意識到:教育不是重復,而是喚醒;教師不是傳遞知識的管道,而是點燃火種的人。
從“完成任務”到“看見孩子”
剛參加工作那幾年,我滿腔熱血。每天提前半小時到校,把教室打掃得一塵不染;課后為學生逐字批改作業,寫滿鼓勵的話語;周末還主動家訪,了解每個孩子的成長環境。那時的我,像一臺永不停歇的機器,用盡力氣去“做好”一名老師。
可十年過去,熱情悄然褪色。備課變成復制往年教案,課堂成了知識點的堆砌,評語也漸漸簡化為“不錯”“加油”這樣的套話。我開始習慣性地問自己:“這節課要講什么?”卻很少再問:“孩子們需要什么?”
直到那次作文里的那句話,像一記耳光把我打醒。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——我不是在“教語文”,而是在通過語文,幫助孩子認識世界、表達自我、建立思維。
于是,我決定改變。不是為了評職稱,不是為了應付檢查,而是為了不辜負那一雙雙望著我的眼睛。
讀書,是教師最樸素的修行
我重新拾起閱讀。不是隨便翻翻,而是有系統地讀。蘇霍姆林斯基的《給教師的建議》讓我明白,真正的教育始于對人的理解;佐藤學的《靜悄悄的革命》教會我如何傾聽課堂中的“微小聲音”;王榮生的《語文科課程論基礎》則幫我厘清了語文教學的本質。
我發現,很多我以為“理所當然”的教學方式其實并不科學。比如我們常讓學生背誦好詞好句,美其名曰“積累”,但如果沒有真實的表達需求,這些詞語就像無根的浮萍,飄一陣就散了。后來我在教學《秋天的雨》時,不再要求學生機械摘抄,而是帶他們去校園里觀察落葉,聞泥土的氣息,然后用自己的話寫一段“我眼中的秋天”。
結果,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的孩子寫下:“秋天的雨不像夏天那么急,它慢慢地,把樹葉染成金黃色,好像時間也慢了下來。”——這才是語言的生命力。
讀書不僅改變了我的教學方法,更重塑了我的教育觀。我開始明白,教師的專業成長,從來不是靠培訓聽來的技巧,而是靠持續閱讀與思考沉淀下來的判斷力。
走進課堂,也走進同行的課堂
過去,我總覺得自己的課“還行”,直到我第一次走進同事李老師的課堂。
那是一節二年級的識字課。她沒有直接教“休”字怎么寫,而是畫了一棵樹,然后說:“一個人走累了,靠在樹下休息,這就是‘休’。”孩子們立刻笑了,紛紛模仿動作。接著她又引出“體”“依”等字,整個過程像講故事一樣自然。下課后,一個孩子跑過來問我:“老師,‘林’是不是兩棵樹站在一起說話?”
那一瞬間,我突然懂了什么叫“漢字思維”。
從此,我開始主動去聽不同年級、不同學科的課。我發現數學老師講“分數”時用切蘋果的方式演示,科學老師帶學生在操場上測量影子長度來理解時間變化……這些看似簡單的做法背后,是對兒童認知規律的深刻把握。
我也開始參與教研活動,不再只是點頭附和,而是敢于提出疑問:“為什么這篇課文一定要分段落大意?”“我們設計的練習真的能檢測理解嗎?”起初有些尷尬,但漸漸地,討論變得真實而深入。我們甚至一起嘗試打破單元界限,設計跨學科的主題學習,比如以“橋”為主題,結合語文閱讀、數學測量、美術繪畫和科學實驗。
原來,成長從不是孤獨的跋涉,而是在彼此照亮中前行。
教學研究,從“經驗主義”走向“反思性實踐”
以前我也寫教學反思,但大多是“本節課時間安排不夠”“學生回答不積極”這類表面問題。現在我學會了追問:為什么學生不積極?是問題太難?還是他們覺得沒有表達的安全感?有沒有更好的切入方式?
有一次教《小英雄雨來》,我發現孩子們對“抗日戰爭”缺乏基本概念,講得再動情也難以共鳴。于是我調整教學設計,先播放一段當時兒童生活的真實影像,再讓學生對比自己和雨來的日常生活。當一個孩子說“他比我大不了幾歲,卻要面對槍炮,而我還在為作業多抱怨”時,全班安靜了。
課后我記錄下這個細節,并進一步查閱資料,了解戰爭背景下兒童的心理狀態。這種基于真實問題的研究,讓我逐漸擺脫了“憑感覺上課”的慣性。
我開始嘗試做小型的行動研究。比如針對學生寫作畏難的問題,我設計了一個“每日三句話”計劃:每天放學前,每個學生用三句話記錄當天最難忘的一件事。不評判語法,不限制內容,只強調“真實”。堅持一個月后,很多孩子從最初的“今天吃了雞腿”慢慢發展到能寫出細節和感受。期末作文時,竟然有學生主動寫起了連載故事。
這些微小的探索讓我體會到:教育研究不是專家的專利,而是每一位教師都可以進行的專業實踐。
基本功,是托起課堂的底色
在這個多媒體盛行的時代,有人覺得板書、朗讀、書寫都不重要了。但我始終相信,教師的聲音、筆跡和姿態,本身就是一種教育。
我重新練習粉筆字。每天上課前,我會提前十分鐘到教室,在黑板上工整地寫下課題和關鍵詞。有次一個學生悄悄告訴我:“老師,我最喜歡看你寫字,一筆一劃都很有力氣,像在跳舞。”
我也開始重視朗讀。以前總是讓學生齊讀,現在我會示范朗讀。讀《荷花》時,我放慢語速,輕柔地念出“白荷花在這些大圓盤之間冒出來”,教室里突然變得特別安靜。課后有家長反饋,孩子回家模仿我的語氣讀課文,連爺爺都說“聽著真舒服”。
這些看似“過時”的基本功,恰恰是最能傳遞情感的媒介。它們讓知識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,而是帶著溫度的聲音和畫面。
教育,是一場雙向的滋養
最讓我感動的是,當我開始真正關注學生時,他們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應我。
班上有個男孩長期不交作業,批評無效,談心也沒用。后來我偶然發現他特別喜歡畫漫畫,于是提議他用圖畫形式“交作業”——把課文內容畫成連環畫。他眼睛一下子亮了。第一幅畫交上來時,雖然線條稚嫩,但情節完整,人物生動。我在全班展示,并說:“這是另一種形式的閱讀理解。
”從那以后,他不僅按時完成圖畫作業,還主動開始寫文字說明。
還有一個女孩,性格內向,從不舉手發言。我在她的日記本里發現她寫了很多小詩。我沒有當眾表揚,而是在她生日那天,把她的詩悄悄打印出來,配上插圖,做成一本小小的詩集送給她。第二天,她紅著眼睛遞給我一張紙條:“老師,這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寫的東西有人認真看過。”
這些瞬間讓我明白:所謂教育,不是我們單方面地“給予”,而是在彼此看見中共同成長。
在倦怠中尋找出路
當然,我也經歷過低谷。去年期末,連續加班改卷、寫評語,身體亮起紅燈。醫生說:“你這是典型的慢性疲勞,需要休息。”那一刻,我突然意識到:一個疲憊不堪的老師,怎么可能帶給學生生機勃勃的課堂?
于是我開始調整節奏。不再追求“完美教案”,而是留出更多時間觀察學生;不再事事親力親為,而是培養班干部參與管理;周末盡量不工作,陪家人散步、看書、聽音樂。奇怪的是,當我放松下來,教學反而更有靈感了。
我終于懂得:教育不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,而是讓自己先成為一盞燈——穩定、溫暖、可持續。
寫給所有在路上的教育者
如果你也曾在講臺上感到疲憊,如果你也懷疑過自己的價值,請相信:每一個想要變得更好的念頭,都是珍貴的。
不必追求成為“名師”,不必非要發表論文或獲獎。只要你還在思考“怎樣對孩子更好”,還在嘗試新的方法,還在為某個孩子的進步而欣喜,你就已經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教育的意義,從來不在宏大的口號里,而在你為一個孩子多等的那一分鐘,為你在備課時多查的那一頁資料,為你在批改作業時多寫的一句真誠評語。
這條路沒有終點。我們無法保證每個孩子都成才,但我們可以保證:當他們回望童年時,至少有一位老師,曾認真地看過他們,聽過他們,相信過他們。
而這,就是教育最樸素也最深遠的力量。
 搜索教員
搜索教員

最新文章

熱門文章
- 殷教員 中國政法大學 英語
- 嚴教員 清華大學 數學
- 辛教員 新疆大學 師范類物理學
- 王教員 北京語言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
- 張教員 北方工業大學 微電子科學與工程(集成電路的設計與測試))
- 徐教員 香港的大學 經濟學
- 周教員 北京語言大學 英語和高級翻譯
- 陳教員 貴陽學院 漢語言文學
- 吳教員 北京大學 藥物制劑
- 王教員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保險精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