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語文教學中尋找光:一位教師的研修覺醒與教育沉思
【來源:易教網 更新時間:2025-10-11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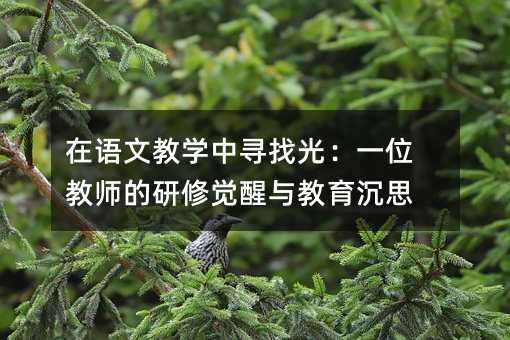
我曾經以為,教語文就是教字詞、講段落、劃重點、做練習。一支粉筆,一本教材,一張試卷,構成了我課堂的全部。直到那次參加陜西省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訓,我才意識到,原來我一直在用昨天的方式,教著明天的學生。
那段時間,我坐在屏幕前,聽專家們娓娓道來。他們不念稿,不空談,而是用真實的課堂案例、鮮活的學生反應、深刻的教育觀察,一點點撬動我固化的教學思維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教育不是灌輸,而是點燃;教師不是權威,而是引路人;語文課,不該只是知識的搬運,更應是思想的喚醒。
從“教書”到“育人”:理念的悄然轉變
培訓中,我第一次認真思考“語文”到底是什么。它不只是中考的120分,不只是背誦默寫的任務清單。它是語言的運用,是思維的訓練,是情感的共鳴,是文化的傳承。當我把《背影》僅僅當作一篇閱讀理解題來講解時,我其實已經錯過了它最動人的部分——那個沉默父親背后的愛與犧牲。
我開始嘗試改變。在講《孔乙己》時,我不再只分析人物形象和主題思想,而是讓學生設想:如果你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計,你會怎么看待孔乙己?你會嘲笑他嗎?你會同情他嗎?如果他是你身邊的某個人,你會怎么做?
學生們的回答讓我震撼。有人寫:“我可能會笑他,但笑完會后悔。”有人寫:“他讓我想到小區里那個總撿廢品的爺爺,其實他也有尊嚴。”這些文字不再是標準答案的復刻,而是真實情感的流淌。
我突然意識到,語文課的真正價值,或許不在于學生記住了多少知識點,而在于他們是否開始用文字表達內心,是否開始對世界有了更細膩的感知。
這種轉變,源于理念的更新。我開始把新課標中的“核心素養”四個字,真正放進心里。語言建構與運用、思維發展與提升、審美鑒賞與創造、文化傳承與理解——這四項,不再是墻上貼的標語,而是我每節課設計的出發點。
比如在教《春》這篇課文時,我不再滿足于讓學生找出比喻句和擬人句,而是引導他們思考:朱自清為什么寫“小草偷偷地從土里鉆出來”,而不是“長出來”?一個“偷偷地”,傳遞了怎樣的情緒?春天在作者筆下,為什么是“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”?這種觸覺的描寫,又喚起了你怎樣的記憶?
當學生開始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去對接文本,語文就不再是遙遠的符號,而是可以觸摸的生命體驗。
教師角色的重新定義:從“講授者”到“共學者”
培訓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:“教師不是知識的終點,而是學習的起點。”這句話像一束光,照進了我長久以來的盲區。
過去,我總覺得自己必須“懂一切”。學生一提問,我就得立刻給出標準答案。一旦答不上來,就會感到尷尬甚至焦慮。但培訓中一位專家說:“最好的課堂,是老師和學生一起‘卡住’,然后一起想辦法解開。”
這句話讓我釋然。于是,我開始在課堂上說“這個問題我也不太確定,我們一起查查資料”;開始在作文批改中寫下“這一句讓我很感動,能和我分享你是怎么想到的嗎”;開始在討論中說“你的觀點和我不一樣,這很有意思,能說說理由嗎”。
學生反而更尊重我了。因為他們感受到的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,而是一個愿意傾聽、愿意學習的伙伴。
有一次講《桃花源記》,一個學生突然問:“老師,陶淵明寫的桃花源,是不是有點像烏托邦?現實里真的存在這樣的地方嗎?”我愣了一下,隨即說:“這是個特別好的問題。我們能不能一起找找,歷史上有沒有人真的試圖建立過類似桃花源的社會?”
那節課,我們臨時改變了計劃,分組查閱資料。有學生找到了“空想社會主義”中的“新和諧公社”,有學生提到了中國古代的“避世隱居”傳統。雖然這些內容超出了課本范圍,但學生的眼神是亮的,思維是活躍的。
我漸漸明白,教師的角色,不是“給出答案的人”,而是“提出問題的人”。不是“知識的搬運工”,而是“思維的點燃者”。真正的教育,是讓學生敢于質疑,敢于探索,敢于在未知中前行。
學生角色的重新發現:從“接受者”到“創造者”
我們常常說“以學生為中心”,但怎么做才是真正的“中心”?
培訓中,我學到一個詞:“學習主權”。意思是,學生應該擁有對自己學習過程的主導權。這讓我開始反思:我的課堂,真的是學生的嗎?
于是,我嘗試做了一些改變。比如在作文教學中,我不再統一命題,而是讓學生從自己的生活中選題。有學生寫“媽媽的嘮叨”,有學生寫“打游戲被發現的那一刻”,有學生寫“弟弟搶我零食的戰爭”。這些題目“不夠優美”,但足夠真實。
我還在班級設立了“語文角”,鼓勵學生張貼自己的小詩、隨筆、讀書筆記。起初沒人敢貼,我就先貼了自己的幾篇日記。慢慢地,有人開始嘗試。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的女生,貼了一首寫給外婆的詩,最后一句是:“你走后,我學會了煮粥,可總煮不出你煮的味道。”全班讀完,一片寂靜,然后有人輕輕鼓掌。
那一刻,我明白了:語文的最高境界,不是考試拿高分,而是讓人學會表達愛,學會理解痛,學會在文字中安放自己的靈魂。
我也開始嘗試項目式學習。比如在學完八年級下冊的“人與自然”單元后,我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,做一個“身邊的環境問題”調查。他們去小區拍垃圾堆放點,去河邊測水質,去采訪環衛工人。最后用文字、圖片、數據做成報告,在班級展示。
一個學生在報告結尾寫道:“我們以為環保是大人的事,后來發現,連我們扔的一張紙,都在影響這個世界。”這種覺醒,是任何說教都無法替代的。
終身學習:教師成長的唯一路徑
培訓結束后,我最大的收獲不是學到了多少技術,而是重新點燃了學習的熱情。
我開始每天留出半小時閱讀教育類書籍。讀佐藤學的《靜悄悄的革命》,我明白了“傾聽比發言更重要”;讀李鎮西的《愛心與教育》,我懂得了“教育是心靈的藝術”;讀王榮生的《語文課程與教學內容》,我意識到“教什么”比“怎么教”更關鍵。
我也開始嘗試使用信息技術。不是為了“炫技”,而是為了拓展學習的邊界。比如用音頻軟件讓學生錄制課文朗讀,互相點評;用在線協作文檔,讓全班共同修改一篇作文;用思維導圖工具,幫助學生梳理議論文結構。
但我也清醒地知道,技術只是工具,核心永遠是教育本身。用PPT講滿堂灌,和用黑板講滿堂灌,本質上沒有區別。真正的變革,發生在教師的教育觀發生轉變的那一刻。
我越來越體會到,教師這個職業,注定不能停留在舒適區。知識在更新,學生在變化,社會在發展。如果我們固守二十年前的教學方式,就是在用過去的地圖,尋找今天的路。
“問渠那得清如許,唯有源頭活水來。”這句詩,我教了十幾年,直到這次培訓,才真正懂了它的分量。教師的“活水”,來自持續的學習,來自不斷的反思,來自敢于否定自己的勇氣。
回歸語文的本質:在文字中看見人
回望這次研修,它像一場及時的春雨,滋潤了我干涸的教學心靈。我開始重新審視每一節語文課:我是在教“語文”,還是在教“人”?
當學生讀《背影》時流淚,當學生寫作文時袒露心聲,當他們在討論中爭得面紅耳赤,我知道,語文正在發生它最本真的作用——讓人更像人。
語文課,不該只是分數的競技場,而應是心靈的棲息地。它要教會學生讀懂文字,更要教會他們讀懂生活;要教會他們寫出通順的句子,更要教會他們表達真實的思想。
作為教師,我們的使命,不是把所有答案塞進學生腦子里,而是幫他們點亮心中的那盞燈。那盞燈,叫思考,叫共情,叫獨立,叫希望。
這條路很長,但我愿意一步一步走。因為我相信,每一個認真對待語文的教師,都在悄悄改變著教育的未來。而每一個被語文照亮的學生,都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的光。
 搜索教員
搜索教員

最新文章

熱門文章
- 殷教員 中國政法大學 英語
- 嚴教員 清華大學 數學
- 辛教員 新疆大學 師范類物理學
- 王教員 北京語言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
- 張教員 北方工業大學 微電子科學與工程(集成電路的設計與測試))
- 徐教員 香港的大學 經濟學
- 周教員 北京語言大學 英語和高級翻譯
- 陳教員 貴陽學院 漢語言文學
- 吳教員 北京大學 藥物制劑
- 王教員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保險精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