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讀不吵鬧,掃地不慌亂:一個二年級班主任的日常實錄
【來源:易教網 更新時間:2025-10-12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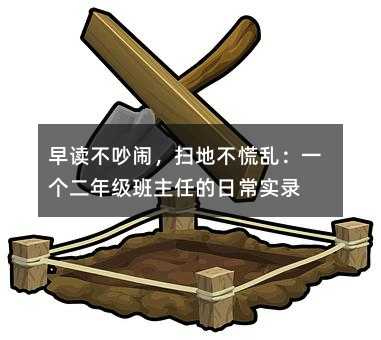
每天清晨七點十分,教學樓前的空地上,五組學生已經站好。一組領讀,一組維持秩序。沒有老師在場,書聲卻整齊劃一。這不是演習,是二年級(3)班的日常。
暑假過后,孩子們長高了,也更“有主意”了。有人賴在門口不肯進教室,有人把課本當玩具,有人掃地時把落葉掃成小山,自己卻蹲在一邊笑。這不是調皮,是成長的痕跡。但成長若無人引導,就容易變成混亂。
我選擇不靠喊叫,也不靠懲罰。我從最具體的事開始:早讀。
班上選出五名學生,每人帶一個搭檔。一個負責讀課文,一個負責提醒坐姿。誰讀得響亮,誰整理了桌角,誰沒遲到,就貼一朵小紅花。花不多,但每天都能看到。一個月后,有人主動提前十分鐘到校,不是為了躲老師,是為了多貼一朵花。再過兩個月,沒人再等老師來催。書聲自己起來了。
掃地是另一個難題。
學校分了室外清潔區,面積不小,落葉一刮就是厚厚一層。大掃把比人還高,孩子舉不起來,掃兩下就喘。有人干脆把葉子堆成堆,轉身就跑。我每天早到半小時,不說話,先拿起掃把,示范怎么握、怎么壓、怎么轉圈。他們圍在邊上,看。看了一周,有人試著學。兩周后,有人主動問:“老師,我這樣對嗎?
”三個月后,即使我請假,他們也能在十分鐘內把整片區域掃干凈,連角落的紙屑都不留。
不是他們突然變乖了,是他們明白了:事情要做,而且可以做好。
路隊也一樣。
學校要求集會時必須排成直線,腳步一致,不說話,不東張西望。我們班過去做得不錯,但我沒覺得可以松口氣。一次升旗,有個孩子偷偷回頭和后排說話,隊伍就歪了。我當天沒批評他,第二天在班上開了個短會,叫“雁群飛行我站隊”。
我說:“大雁南飛,為什么從不亂飛?因為領頭的飛得穩,后面的跟著,不搶不掉隊。我們站隊,不是為了好看,是為了安全。你一亂,全班都得停。你站得直,別人就跟著穩。”
那天之后,我每次集會,都第一個站好,不看手機,不低頭,不說話。孩子們看在眼里。沒人再提“我昨天沒站好”,但隊伍越來越齊。期末評比,我們班拿了“最佳路隊獎”。獎狀貼在墻上,沒人特意去夸,但每天經過時,都有人多看一眼。
活動不是湊熱鬧。
九月,奧運剛結束。我沒講“為國爭光”的大道理,只是問:“你們記得哪個運動員摔倒了又爬起來?”有人說是體操隊員,有人說是游泳選手。我說:“對,他們沒說‘我一定要贏’,他們只說‘我再試一次’。”那天的班會,孩子們寫了一張張小紙條,貼在墻上:“我下次數學錯題,再算一遍。”“我今天沒背完課文,明天早起背。
”
教師節,我們沒送賀卡,而是約定:上好每一節課,寫好每一次作業。作業本上,有人畫了小太陽,旁邊寫著:“今天沒抄錯字,老師別生氣。”
中秋節,我們帶了一個蘋果,寫上名字,放進慰問箱。孩子問:“解放軍叔叔吃蘋果嗎?”我說:“吃,但他們可能很久沒吃新鮮的了。”沒人再說“我不要帶”,因為大家知道,這不是任務,是心意。
十月,國慶長假,我布置了一個作業:用相機、畫筆,或者一首小詩,記錄你眼中的祖國。不是“偉大的祖國”,是你家門口那棵長了十年的梧桐,是你奶奶蒸的桂花糕,是你爸爸騎車帶你去公園的那條小路。交上來的作品里,有孩子畫了一只斷了翅膀的風箏,下面寫著:“爸爸說,風箏飛不高,是因為風不夠大。
但風一直在,所以它還會飛。”
神舟飛船升空一周年那天,我們沒看視頻,沒做PPT。我帶他們去操場,仰頭看天。我說:“那顆星星,是人造的。它飛得比鳥高,比云遠。你們知道嗎?它上面的螺絲,是中國人一顆一顆擰上去的。”沒人說話,但那天放學,好幾個孩子跑回來問我:“老師,你能借我一本講火箭的書嗎?”
這些事,沒有獎狀,沒有分數,也沒有人寫進總結報告。但它們在孩子心里,悄悄生了根。
我不信“一教就會”,也不信“不打不聽話”。我只信:孩子需要的,不是被管住,而是被看見。被看見他們的努力,被允許犯錯,被陪著一點一點改。
他們不是小大人,但也不是小動物。他們是正在學習如何成為自己的人。
早讀時的書聲,掃地時的汗水,排隊時的沉默,作業本上的小太陽——這些都不是“教育成果”,是生活本身。
而教育,不過是把生活,過得更有溫度。
 搜索教員
搜索教員

最新文章

熱門文章
- 陳教員 貴陽學院 漢語言文學
- 吳教員 北京大學 藥物制劑
- 張教員 中國農業大學 土地科學類
- 夏教員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經濟學
- 梁教員 重慶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
- 冉教員 清華大學 應用經濟學
- 孫老師 大學講師 應用經濟學
- 鄭教員 首都師范大學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
- 蘇教員 華中科技大學 公共管理
- 蔡教員 北京郵電大學 電信工程及管理
